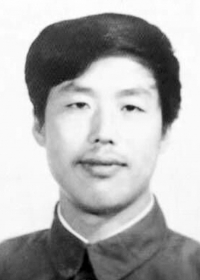- 2024年1月18日 星期四
- 社长:赵宝泉 总编辑:周钢
一盏灯火,点亮一段故事
2024年1月18日
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此情此景,充满无尽温馨。 夜幕笼罩,远望一家家灯火时,你是否会好奇,每一处光亮下有着怎样的人、过着怎样的日子?一盏灯火,照亮一家生活。 只是,这生活未必全是幸福,或许不免艰辛。何况,灯火自身的变更,何尝又不是流水岁月的注脚? 桐油灯 围坐火塘边听父亲讲三国 讲述 卓育训 83岁 来自 广东广州 我老家在湘西,至少上世纪50年代以前,各家各户常用的照明用具均为桐油灯。关于桐油灯,我最深的记忆是听父亲讲三国故事。 掌灯时分,我们一家老小,有时还有邻居家的伯父、堂兄弟,大家围坐在火炕屋的火塘边。父亲坐在靠墙的坐桶里(圆形木桶,铺稻草覆以棉垫),两手捧着书,凑近光照有限的桐油灯,眯着眼睛看,有时眉头紧皱,有时微微一笑——那专注的神情,在我脑海里至今清晰如昨。父亲看了一会便合上书本,一本正经地开讲。 平日里父亲不苟言笑,给我们说起三国却是声情并茂,听得我们跟着高兴或难过。桃园结义、三顾茅庐、火烧赤壁……父亲不知道讲了多少晚,反正一直讲到诸葛亮病逝。我们总是不愿睡觉,央求父亲再看再讲。每晚,桐油灯都由母亲管理。不时看到母亲给灯盘加油,或是用小棍点拨灯芯。父亲看书时用两根灯芯,讲书时则只用一根,以省桐油。我们总是暗暗生气,嫌母亲动来动去,干扰我们的浓兴,当然不敢说,不能说。 其实,那时候特别穷困的人家连桐油灯也用不起,晚上只能黑灯瞎火,或是点燃不要钱的松节、草把照亮。 马灯 灯光大了些,父母干仗 讲述 王开顺 56岁 来自 江苏盐城 我父母退休前在木帆船上工作,晚间航行,小马灯是照明灯具。白天,父亲取下玻璃灯罩擦拭干净,再扭开灯座上的盖子添上火油。火油也被称为洋油,其实就是煤油。买洋油要花钱,因此,马灯一般只在晚间吃晚饭才舍得用。在行船时,就把灯捻子捻得很微弱,光线黯淡,摆放在母亲摇橹的橹绳下。这样做,一是为了省油,二是可以让灯罩慢一点被熏黑。 有一次,也不知父亲是不是因为干活累了无处释放,回船后看到母亲在捻子稍大一点光下忙活,不问青红皂白,先是大吼一声,然后又捶了一下母亲后背。那时,父亲是一家之主,大男子主义特别强。他觉得母亲浪费洋油,比割他身上的肉还要心疼。母亲也是气不打一处来,与父亲扭打起来。两个人打得船直摇晃,后被别人拉住才停止。父母因为家务事几乎争争吵吵了一辈子,但也不离不弃地过了一辈子。只是这次干仗,让我记忆特别深刻。唉,那个艰难的年代呀…… 电石灯 灯光照亮一生姻缘 讲述 郭德诚 70岁 来自 河南洛阳 1979年,停电是常有的事,家家都有自备灯。当时有一种自制的“电石灯”,靠电石和水反应产生乙炔气体,点燃后非常亮。我在厂里干机修钳工,小院里四家的电石灯都是我做的。邻居张大娘说,这比洋蜡亮多了,还不花钱。后来,张大娘给我介绍了个对象,是街口卖烧鸡杨伯家的闺女。姑娘漂亮,我的条件也还行:退伍军人,国营大厂职工。可是,我俩一直处得不温不火。 下夜班时,我总能看到杨伯的烧鸡摊。他用着一个小电石灯,灯不亮,小摊半明半暗。那天没事,我用一截废钢管做了一个大电石灯。我用废铜管做灯管,还做了两根细钢针,可以用来疏通灯管。又做了一个密封小罐,用来储存备用电石。做完反复打磨,涂上了白漆,看上去很漂亮。又和姑娘约会时,我带上了这套东西,她很意外。后来,我再下夜班,见杨伯的小摊亮多了。那大电石灯效果就是好,摊上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。不久,张大娘笑眯眯地告诉我:“小子,你这事成了!老杨两口子同意了。”我心中一阵狂喜。张大娘说,那两口子可是很挑剔的,没想到你小子不哼不哈,把事办成了。 我当时是个愣头小伙子,没想到做了个电石灯,竟把我婚姻的路给照亮了。1980年,我就和对象结婚了。 电灯 电灯亮起来小孩跳起来 讲述 曹银员 71岁 来自 浙江宁波 我在浙北岱山岛一个小村里长大。1970年初春,我们村从上海购买来一台柴油发电机,建机房、立线杆、接电线,家家户户装上了灯泡。那天晚上,父亲满脸笑容地伸手一拉开关,屋子里瞬间明亮起来。“来电啦!灯泡亮了!”我激动地喊了起来。四合院里,几名小朋友也像着了魔,兴高采烈地来回转圈,高喊“毛主席万岁”。 更可喜的是,1973年3月岱山电厂成立,岛上各个乡镇陆续通电。不过,那时候照明用电是有限制的。一般到了晚上8点半,当班的电力工人会通过连续三次开关电,提醒用户马上就要断电了。那时电力装机容量小,线路设施差,经常停电。电灯与煤油灯及蜡烛互补照明,成为那个年代多数家庭的选择。 煤油灯 到邻居家“借光”念书写字 讲述 刘振广 75岁 来自 河北滦南 上世纪60年代,我们那里农村还没有电。冬天黑得早,我和三个妹妹、父母挤在土炕上的灯台旁,写字的写字,做活的做活。一天,对门大伯来找父亲,看到灯下情景,忍不住笑了:“你家这小油灯利用率可够高啊!”母亲说:“孩子们都念书,不这样咋办?”大伯说:“你看侄子侄女写字,胳膊肘都碰胳膊肘了。这样吧,让侄儿晚上到我家去学习,我家灯下宽绰。”我读高小,每天要做一个多钟头功课。见大伯态度坚决,我父母便同意了。其实,伯父伯母和我家并没有血缘关系,就是住对门的邻居。他家两个闺女出嫁了,家里只有老两口。平时伯母很喜欢我,常给我留好吃的。 从那天开始,我到大伯家借光学习。煤油灯结了灯花,伯父伯母赶紧拿剪刀剪掉。明亮起来的灯光,激励我学习更加用心…… 短发言 1976年,我和弟弟结伴回湖南老家插队,老家尚未通电,照明全靠煤油灯。那时,高级的煤油灯要花钱买,它有玻璃罩子防风,还可以调节亮度。点燃时,油烟通过罩子袅袅升起。普通灯都是自制的,用墨水瓶或其他玻璃瓶子装上煤油,用牙膏皮做成管,再将棉灯芯放入其中,点燃时油烟弥漫,光线摇曳。在这种煤油灯下做事,不多久就把人熏成“包公”。(湖南衡阳 唐锦荣 66岁)